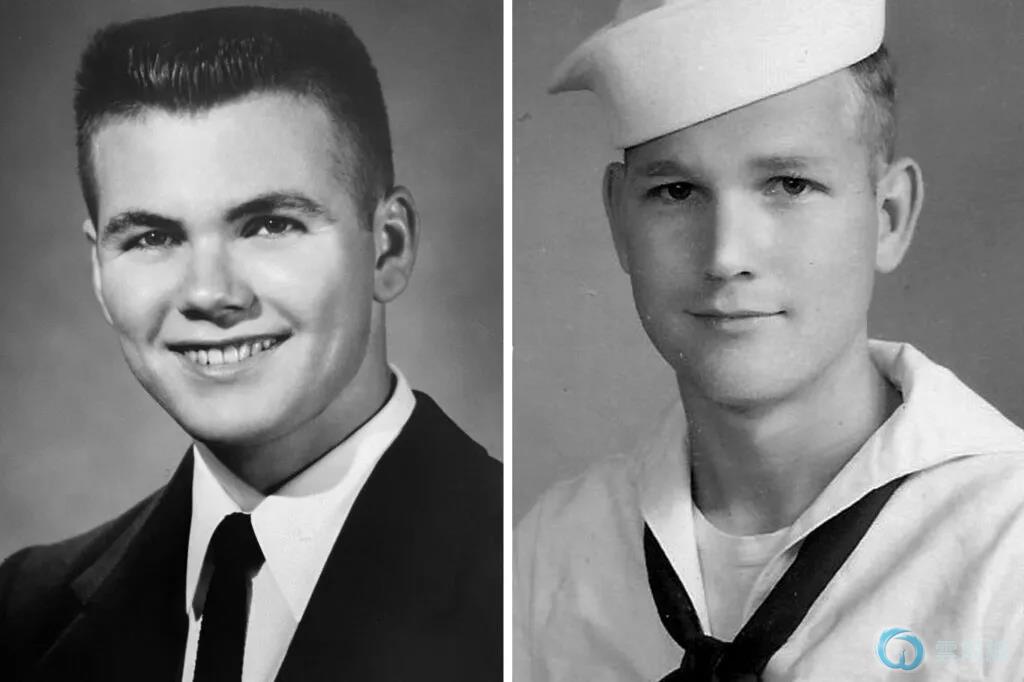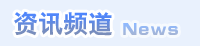 |
|

杨振忠把自己肥厚性感的嘴唇摄制成特写,像煞了鱼嘴,也像煞了人体上另外两种黏膜洞隙,然后很负责任地播放到鱼缸里,然后又煞有介事地让它反复发音,声称“我们不是鱼”,首先乱伦了人类和鱼类,其次就是乱伦了器官的属性、分类和分工。仅仅是一个作品,《鱼缸》,杨振忠就把我们都给颠覆了:我们的嘴跟鱼其实没什么两样,就看从什么角度看;我们的嘴其实与肛门和阴道没什么两样,就看怎么用;我们的类别并不是万物的灵长,就看是不是被淹没在水里……
于是乎,酷儿诞生了,我们反而解放了。
有些男人喜欢女妆,天生天然地喜欢。有些女人喜欢女人,天经地义地喜欢。有些男人想变成女人,不怕手术之苦,天理昭彰人理卓著地喜欢。大胆地、勇敢地、忘我地表达曾经被主流话语打入冷宫的殊异天性,就是酷儿。酷儿的行为哲学是,想穿什么穿什么,该喜欢什么人就喜欢什么人,自己认为是什么性别就取什么性别姿态,想把自己的嘴打扮成鱼、成鸟、成兽、成花朵,都很创意。
酷儿一词借典自中国台湾。台湾酷儿借典自英文Queer。Queer原文原本是咒骂同性恋者的粗话纪大伟和但唐谟在《岛屿边缘》季刊“酷儿专辑”中译成“酷儿”时,英文的诅咒色彩已尽失去,挑衅使而俏皮、酷异而炫惑、促狭使性而又光怪陆离的新文化色彩反而十分耀目。在中国译文和既存文化脉络中,找不到它的渊源。的出现,意味着崭新情感历史的创篇。
“酷儿”当机而生,它跨越或曰超越认同。在同志文化强调同志的所谓正面形象、正面情谊的时代,酷儿文化调整姿态,不以主流文化霸权所肯首的“美好”条件作为自身建设的标准。妖异,殊奇,怪诞,佻达,信口雌黄,任意妄为,但凡能对霸权文化形成挑衅和挑战的资质都被兀显出来。它拒绝定性,拒绝被归类,拒绝使用早已被霸权化了的“好”的标准也拒绝群体观念。
主流文化主张认同,主张新的全球一体化、世界大家庭,酷儿却不相信单纯认同。它在任何准则之外游弋,并不讲时机地对准则施行嘲弄或暴力。纪大伟在概括台湾酷儿文学的特点时指出,“酷儿文学的第一项特色就是呈现身份的异变与表演。为了挑逗固有的身分认同,酷儿文学经常出现身份不明确的角色”,“第二项特色,即呈现欲望的流动与多样”。譬如纪大伟本人的中篇小说《膜》的主人公桃子,就既是男孩又是女孩,既喜欢过异性也喜欢同性甚至连自己的性别都分不清楚。它由此批判传统的性别划分、性别权力、及任何歧视。
作为同志文化的延展,酷儿理论与实践提示着跨越性别界限,不以性别决定人际关系、家庭或社会结构“新社会”诞生之可能性。原有的社会集结方式,往往以习俗的沿袭为根据,缺乏创造性。酷儿精神则在同志文化中看到一种更改文明本味的力量。原来是受排挤、受歧视、在挣扎中为自身正名的边缘文化/异殊文化,经过酷儿理论的照亮,被推衍为革命性、创举性的先锋精神。“它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广义的文化,一种发明出新的人际关系、生存类型、价值类型、个人之间的交往类型的文化,这一文化是真正全新的,与既存的文化形式既不相同,也不是添加在既存的文化形式之上。”(Halperin)
我曾宣称:发现一切爱的潜能,身体的,超越身体的,有限的和无限的。抛开习俗的,道德的,历史的,立法的,种性的,抛开一切拘束和框限,打造出一个新人类欲望版图,或者说用解放的法则重塑爱情的、官能的、欲望的新国际。
酷儿就是这样,主张看似乖张出格、实则自由松弛,钻研和开发身体、官能情谊、本有的各种可能性。纪大伟说,“酷儿是拒绝被定义的,它没有固定的身分认同”。他们仅仅是一些她她他他的个人,不是“他们”,在欲望新地图上,她她他他每一个都意味着一种国界,随时可以描上颜色,又随时可以抹掉,可以画成新的国度、新的彩色。“酷儿无形无状”,它登上已衰老蜕化的文化陆地,革新和改造固步自封的一元中心或二元对立的朽腐模式。
酷儿像一群化了妆、穿着小丑服装(当然是千奇百怪)、嬉戏顽皮又聪颖绝顶的孩子,一个人或一群人总是在过十足的狂欢节。然而,我们会吊诡地说,我们不是鱼,我们不是嘴,我们不是器官,我们不是鸟,我们不是走兽,我们不是花朵,我们不是酷儿……
|
|